石马江号子——我的返乡笔记之四十四
石马江是一条流淌着诗意与力量的河流。晋代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记载:“溪水东得高平水口,水出武陵郡沉陵县首望山,西南径高平县南,又东入邵陵县界……”因此她在古代的学名被称为高平水。然而隆回县高平镇的先民们并不讲究这些,只觉得一条大河波浪宽,于是就叫她“大河”了,这一叫就叫了几千年。

大河穿过茂密的丛林,流经我的家乡新邵县迎光乡境内,经山口里,两岸青山对峙,岸上有个巨大的“屁股印”,据说是远古时期的神仙为了疏通河道,情急之下坐在地方把山门蹬开而留下的,这段河就叫成了“屁股印河”。也有人干脆叫她“顺水河”,因为她流经顺水村。
因此在我的记忆里,是没有石马江这一印象的。
直到我初三那年,一次去县城参加比赛,途经新田铺一个渡口,客车要搭乘轮渡才能过江。等船的间隙,老师望着波涛汹涌的大河,告诉我这叫石马江,我们的母亲河,发于望云山,流经隆回的高平、我们的家乡新邵迎光后,经过龙溪铺、巨口铺、小塘等几个乡镇,再从这新田铺镇的大禹庙村注入资江。我们家那边的大河就是这条河的上游。我才第一次知道,原来叫了几千年的“大河”还有另外一个名字——石马江。

大河的两岸多山,大凡要建房垦田筑坝,采石是必不可少的环节。采石很花费气力,我小时在山野里经常看到石工们光着膀子,搭着汗巾,烈日下一齐“依火里嗨,呀伙哩嗨”地喊着,那声音震动山川,铿锵壮阔。只是后来我慢慢长大,离家乡也渐行渐远,那些古老的、原始的、粗犷的号子声也就在记忆中渐渐淡化了。
去年五一返乡,新邵县政协主席邹功树先生极力向我推荐石马江号子,并介绍说这是家乡极为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县里想重点将其打造成家乡的文化名片。我听后当时脸上微微有点发热,我自诩为一位文化爱好者,竟然对邹主席嘴中的石马江号子一无所知,看来我对家乡的文化还缺课不少。带着几分好奇,在邹主席的带领下,我得以深到新邵县新田铺镇的王理亮老人家中,探寻石马江号子的魅力。
(一)
与周边其他的民居相比,王理亮老人家的房子虽然有点历史,但似乎更多了几分霸气与庄严。别人家的房子基本都与地面齐平的,但他们家的房子却显得格外的高高在上。上他家得先上十几个台阶的楼梯,然后再跨过一座桥,如果没记错的话,桥还要横过一条窄窄的巷子。
这给了我一种朝圣般的感觉。

王理亮老人早早地候在了门口,看到我们到来,忙张罗着给我们倒茶。
这是一位精神矍铄的老人,手脚很是利索,尤其声音极为洪亮,不知道是不是跟他经常吼号子有关。虽然与我是第一次见面,但我能从老人的眼神中隐约感受到一种期待。
据邹功树同志介绍,王理亮老人今年已经85岁高龄,先后担任过镇里的文化站辅导员、站长,由他挖掘、收集、整理及创作的石马江劳动号子和石马江民间故事在当地广为流传。2018年,他被评为石马江号子的省级传承人。
“既然都是省级文化遗产了,为何过去很少听说呢?”主客坐定,我迫不及待地向王理亮老人抛出心中已久的疑问。
王理亮眼神一亮,爽朗地说:“周总,你说得对啊。其一呢,石马江号子属于长期散落在民间的石工号子、渔歌号子等的统称,基本上是我到文化站工作以后才开始全面收集、整理,后来提炼成石马江号子这一文化遗产,因此严格来说这个官方说法时间还不是很长;其二呢,过去咱们石马江流域石工非常多,但现在你也看到,生产发展了,采石大家都用机器,石工越来越少了,唱石马江号子的场景也就越来越稀有了。唱的人少了,自然就很少听到了。”

不用我提问,王理亮老人似乎一下子打开了话匣子。
“石马江号子是石马江流域独有的劳动号子。我19岁开始做石匠,一下子就迷上了。石工喊着号子,才能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帮忙的小工也能应和,有时路过的人也能跟着一起喊,‘依火里嗨,呀火里嗨,嗨哩着哩,嗨哩着哩……’”
老人说着说着,情不自禁地唱了起来,腰杆挺得直直的,脸上放起了光彩,眼神也变得炯炯有神起来。而老人随口唱出的号子,则像一股陡急的山风,在偌大的堂屋里回旋,纯朴而不带任何杂质,嘹亮而又悠长动听。
然而,有那么一瞬间,我心里似乎突然被什么击中了一下。
“等等,您刚才唱的能再唱一遍吗?”所有人的目光停在了我身上。
“您把刚才唱的号子再唱一下试试?”我坚持说。

“依火里嗨,呀火里嗨,嗨哩着哩,海哩着哩……”
“停!”我果断地说。
这时我头皮开始发麻,猛然间恍然大悟,搞半天这石马江号子竟然就是我小时候听过的石工吼叫声。搞半天石马江号子其实早就融到我的生活里了,只是我不知道它叫石马江号子而已。正如我从小在石马江流域长大,却并不知道“大河”就叫石马江一样。
原来如此!
我不由得想起初中那次初识石马江的情景。当时我还专门问老师,为什么屁股印河在我们那就不叫石马江呢?老师说,那是因为我们那地方太偏僻,石马江的叫法源于新田铺有一个石马江村,石马江村还有一座石马江桥。显然,这是一个颇有历史与人文底蕴的名字。遗憾的是,当时的老师没有跟我提及过石马江号子。
(二)
在老人激情满满的介绍中,我慢慢对石马江号子有了更加清晰的认知。
石马江号子以石工号子和渔歌号子为主。
石工号子有二十多种,其中分为三声号子和四声号子。三声号子是一人领,数人和,最后一句领和合齐喊,多为抬石头时用。与三声号子相比,四声号子更普遍,用得更多。如开工时用《开台号子》,打炮眼时用《冬格朗号子》,拖拉石头用《唢呐号子》,打料石用《麻阳号子》,甚至石工们聊天时也用号子。
石工号子在不断演变过程中,形成了长号、短号、急号三类,长号用于拉石头,短号用于撬石头,急号用于抬石头上坡过坳。一旦吼起来,长号如松涛,短号似裂帛,急号若奔雷,既有山歌般的质朴,同时还含有古梅山祭祀歌的那种神秘。
与石工号子不同,渔歌号子则以抒情柔美的声腔为主。此外,还有一些从石马江号子里演变出来的龙灯歌、打铁歌、儿歌和朝圣唱的南岳歌等。
据邹主席说,20世纪五十年代末,石马江畔的80多位石工,曾受新邵县委的派遣,专程赴北京参与修建人民大会堂。他们一边劳动,一边唱着家乡独有的石工号子,受到首都人民的喜爱,都说:“劳动者之歌好听啊!”这成为石马江流域人们最大的骄傲。

但要说让石马江号子真正从民间走上正式舞台,还得感谢王理亮。20世纪六七十年代,王理亮用石马江号子做素材,与县文化馆戏剧干部石景松同志合作创作的《动地歌》首次参加地市文艺汇演,均获好评。这对石马江号子来说是一个全新的起点。
此后的数年,以石马江号子为题材的作品陆陆续续走上前台,开始受到文化界的关注。湖南省市文化和旅游部门对石马江号子的曲号、风格、特点进行了分析和调研,一再强调要将这一优秀的民间音乐挖掘开发、保护和利用起来。
2002年,中央电视台专程采访了时已退休的王理亮,全面讲述了他采集整理石马江石工号子的故事。
这不仅是王理亮老人最高光的时刻,也是石马江号子最高光的时刻。遗憾的是,虽然新邵县有关部门对石马江号子的保护与宣传投入了巨大的精力与资金,但由于整个石马江流域采石工和渔民的几近消失,会唱石马江号子的人还是越来越少了。
“石马江号子是我们石马江人们劳动与智慧的结晶,是石马江人文与历史的见证啊。我最担心的就是,以后石马江号子没人唱了,我们家乡的这一宝贵文化遗产传不下去了。”

听到这里,我突然明白了王理亮老人刚见到我时那股眼神的意思。文化是需要传承的,显然,老人家在为这件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而焦虑。某种程度上,石马江号子已经成为王理亮老人苦心培育的孩子,他希望我甚至每一位慕名而来的客人能为此做点什么。
(三)
石马江号子无疑是深刻的。
如果说石马江是流淌着歌声与希望的画卷,那么,石马江号子则是石马江流域的绝唱与史诗。它不仅仅一种简单的号子,还承载着家乡人们数千年来战天斗地的历史。
网上有文章说,石马江号子起源于元末明初,我不知道这位作者的依据是什么。但凭我的直觉,这个结论显然是草率的。号子作为一种劳动过程中的呐喊,伴随着整个人类文明的进程。商周时代,长江峡江上的纤夫们就开始用号子来协调统一动作。先秦时期的《吕氏春秋》就记载“今举大木者,前呼舆謀,后亦应之”。
石马江流域有着久远的人类文明史,早在距今4000多年前,先民就在石马江的上游繁衍生息,在隆回县高平镇,就有两处龙山文化时期的遗址,一处是小坳遗址,一处为樟树崂遗址。从出土的石刀、石斧等石器看,那个时候的人们就已经采石为器,击石而呼,与石相伴相生。无数的石桥、石墙、石壁、石井、石道见证着这片土地的人们勤劳奋斗的足迹。


在迎光乡,顺水河的北岸就有一条“长不及千尺”的古栈道,系近百名石工劳苦营作,直接在悬崖绝壁上精凿而成,“经年乃开通”。光绪年间县志载:“顺水桥,在高平水左岸,有‘长虹飞渡’磨崖四大字,明县令郑澧阳题。”
在小塘乡,千百年来盛行石匠手艺,石匠们口传心授,世代传承。每年有无数的石匠外出做工。他们业精艺熟,能粗能细,所雕刻的龙、凤、狮、象和“八仙过海”“哪吒闹海”等整套图像,件件精巧玲珑,栩栩如生,其工艺之深和构图之妙,堪称绝伦。
有石工的地方就有号子。可以想象,当石工们手持铁钎,以胸膛抵住岁月,高亢的号子不仅穿透云霄,也穿透了历史。今天的石马江号子不仅传递着先民们“永不言弃”的呐喊,还传递着“我命由我不由天”的精神力量。
石马江号子,还承载着家乡千年不绝奔涌的文脉。
石马江流域自古文风兴盛。上游隆回高平镇,今日看上去偏僻不过,汉代却是一座县城的所在地。三国吴孙皓宝鼎元年(公元266年)分昭陵置高平县。晋武帝太康元年(公元280年)改曰南高平。
中游的巨口铺镇,分布着一佛一道两座楚南名刹。一是文仙观,相传晋代高平县令文斤在此羽化成仙。宋代曾被三位皇帝五次封赏,曾与江西龙虎山道观齐名;另一座叫白云庵,据清道光《宝庆府志》记载:“宋宝佑年间,僧宝鉴披荆斩棘入此山中,知因缘所在,后僧坐化其中”。身居此处,如庵外晓松法师墓塔所刻对联:“目观千里外,身举九霄中”。

下游的新田铺镇,同样有两座古刹闻名遐迩。镇内华盖峰半山腰有一天然“龙宫”古洞,洞口形如龙嘴。明正德年间(1506--1522)南岳上智下光禅师飞锡来此结庐为庵,是名华逸寺。另一处为大禹庙,其所在村就命名为大禹庙村,正是石马江出水口处,江水由此注入资江。清嘉庆《邵阳县志》“卷之五·山川”记载:“县北四十里,石门山上有大禹庙。”“岂非禹之功施于四海而神气则无不之也。”

说石马江号子,不能不说新田铺镇的石马江桥。据残碎断碣查载,石马江桥原名广济桥,系明万历四十四年修成。相传明代万历年间修石马江桥石拱桥时,因桥面石块均重达数千斤,如何搬上成为难题,为首的宝庆知名石匠邓非凡苦思不得其法,一日信步到不远的普照庵外,听到佛歌顿时眼前一亮,马上回到工棚,找到会喊号子的师傅们,将《莲花开》《莲化献佛歌》的韵律融进入石工号子,问题一下子迎刃而解。后大平天国的石达开还为石马江桥留下过对联:“目空天下万人敌,身是吾家千里驹”。

道光十七年,民族英雄林则徐唯一的一次湖南之行,还历经石马江全流域,过石马江桥时记录石马江“水势汹涌,而桥北人家颇盛”,过顺水桥时记录“凿山为路,悬崖突出”,后经屁股印河的山口里入今隆回县境,还到大河边上的颜刘二公庙打了一转。
这些,都已经融入石马江的每一个音符里。
石马江号子作为一种文化形式,必然以这片流域的文化为土壤、为载体、为营养,来源于斯,又相融于斯。听起来是一声号子,细究起来却是这片土地的一种性格、一种传承,更是一种独一无二的地方名片。
(四)
回到北京后,我开始有意识地关注与研究石马江号子的保护与传承。
在我看来,石马江号子这一文化遗产于当地的意义不言自明,不仅仅是传承下去,关键还是让它活起来,火起来。但是要做到这一点,光用传统的方法显然是不够的。
如今的社会环境与以往已经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传承与发展石马江号子,不能再停留在石马江号子的本身,而是要将其视为一种具有深厚底蕴又有无穷爆发力的战略资源,全面融入石马江流域的社会生活,融入当地社会经济发展的进程,借助AI等新的技术、新的场景、新的能量,为其赋能,帮它搭台,助其升级,以新为要,从新出发,如此,石马江号子才能完美传承,大放光彩。

好在我很欣喜地看到,邹功树主席,还有年轻的新田铺镇党委书记黄建桂、副书记廖湘京等一直在竭力为石马江号子的保护与发扬呼吁奔走。去年以来,石马江号子在网络的声量越发多了起来。在多方的努力与协调下,由新田铺镇党委副书记廖湘京作词,廖博作曲,本土歌手石冬演唱,包含有王理亮石马江号子原声的歌曲《记忆里的石马江》2024年登上“星光大道”的舞台,再次借助央视的平台扬名天下。
有理由相信,石马江号子一定会乘着新时代的潮声,以更年轻的姿态在青山碧水间回响;这一传承千年的劳动诗篇,最终会代表家乡化作新时代的文化请柬,邀世界共听一曲生生不息的东方和声。
欢迎关注反映湘中风情的拙作《有一种根叫故乡》。当当、京东商城、亚马逊、天猫等网站有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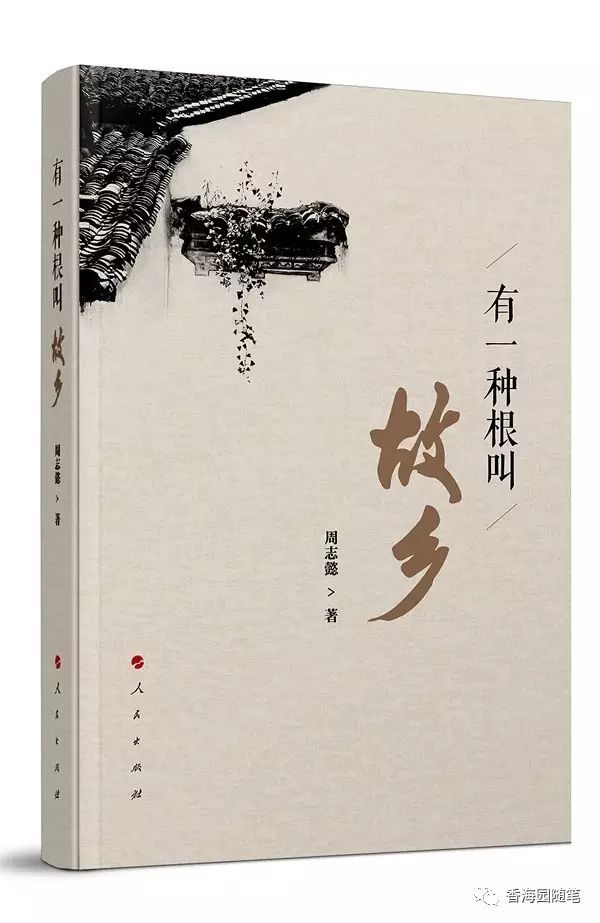
来源:新邵新闻网
作者:周志懿
编辑:兰巧琴